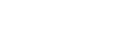车子在峁梁间盘旋时,天已沉下脸来,是一种灰扑扑的、厚实的颜色,像用旧了的羊毛毡。风从看不见的沟壑深处窜上来,带着哨音,硬邦邦地刮在窗玻璃上,呜呜地响。这便是陕北的冬了,来得不声不响,却筋骨铮然。路旁的杨树早已落尽了叶子,只剩下些银灰色的枝桠,偶尔,会有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,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,打破了这份宁静,也带来了一丝生机。春天还远得很。
忽然就想起了儿时。那时的冬,似乎比现在更像“冬”些。清晨,纸糊的窗格子上,总凝着一层厚厚的、毛茸茸的霜花。那霜花是夜的精灵,借着寒气,在玻璃上走笔,画出些奇诡的森林、陌生的海岛,或者干脆就是一片混沌未开的世界。我总爱蜷在被窝里,呵出一小团白气,呆呆地看,直到母亲在灶间拉风箱的声音,“呼啦,呼啦”,将那幻境一点点震落。接着,便是那碗能烫透心窝的钱钱饭了。黄豆压成了小铜钱似的薄片,和着小米,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地熬,香气混着水汽,能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。捧起粗瓷大碗,先不急着吃,只把脸埋在那团暖雾里,鼻尖冻得那点微红,也渐渐化开了。那暖意,是从指尖一路蔓延到胃里,再缓缓升腾到心尖上的,扎实得很,也长久得很。
正出神,路旁闪过一个牵着毛驴的老人。他裹着厚重的黑棉袄,腰间系着布带,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,脸是枣红色的,刻满了和脚下土地一样的沟壑。毛驴的颈下,挂着一只小小的铜铃,随着不紧不慢的步子,“叮——当,叮——当”,声音清亮而孤寂,一下,一下,敲在这冻结了的空气里,传得老远。他没有看我们这陌生的车子,只是眯着眼,望着前方自家的方向。那一瞬间,我忽然觉得,他和他牵着的,不是一头牲口,而是整个冬天的一部分,沉稳,缓慢,与脚下的黄土一般亘古。那铃声,是这片土地上,冬的韵脚。
天色向晚,远处的灯火,一点,两点,继而是一簇一簇地亮了起来,黄晕晕的,像是从大地深处渗出的、隔世的温暖。那温暖,与我记忆里钱钱饭的暖雾,与那老人归家的脚步,与那穿透时空的铜铃声,渐渐地,融成了一体。(薛亚兵)